BOT的全文是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有些观点认为,BOT的实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由政府和企业达成协议,企业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政府向企业颁布特许经营许可,允许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管理和经营该基础设施并获得收益,期满后将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政府和企业之间就上述合作方式而达成的协议就是BOT协议。 部分关于BOT协议的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3〕115号第一条规定:“(二)全部采取特许经营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应全部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实施,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理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转让—运营—移交(TOT)、改建—运营—移交(R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DBFOT)等具体实施方式,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建设和运营期间的资产权属,清晰界定各方权责利关系。”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规定:“(十四)提高新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财政收支平衡状况,统筹论证新建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保证决策质量。根据项目实施周期、收费定价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基本框架和所需要的政府投入等因素,合理选择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运作方式。”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30号)规定:“(二十)拓展对外合作方式。在继续发挥传统工程承包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我资金、技术优势,积极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有条件的项目鼓励采用BOT、PPP等方式,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开展装备制造合作。与具备条件的国家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国际产能合作要根据所在国的实际和特点,灵活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与所在国政府和企业开展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编制)范本(2024年试行版)》:“第10条 特许经营实施方式【说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特许经营项目可合理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转让—运营—移交(TOT)、改建—运营—移交(R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DBFOT)等具体实施方式。此条应明确具体方式,并简述项目交易结构安排等。】” BOT合作模式通常用于投资额度大、运营期限长的项目,一个BOT项目的运营周期往往有十几年至几十年的时间,对于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又缺乏资金的政府是非常方便的方式。不过,恰恰由于运营时间长,而实际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双方负责人可能也会更换,在项目建设完成后的运营期间发生争议的情况并不少见。 BOT协议是行政协议还是民商事协议、因履行该协议产生的争议属于行政争议还是民商事争议,存在较大争议。争议原因可能在于:BOT协议中既包含缔约当事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对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又包括关于特许经营的行政许可内容,有些BOT协议的名称直接就叫《特许经营协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后,由于其第二条规定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因此有些人将BOT协议特别是名称为《特许经营协议》的BOT协议直接视为行政协议,认为相关纠纷为行政纠纷。不过,该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因此,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以2015年5月1日为时间节点,此前签署的BOT协议属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可选择民商事或行政性质。 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笔者认为,BOT协议是行政协议还是民商事协议,不能仅看协议名称,也不能单纯看时间节点,而应当根据BOT协议的具体内容判断协议性质,根据争议的性质确定程序选择。从相关的司法判例看,支持按民事性质审查的法院,一般会以二分法的思维去看待特许经营协议,即将行政协议分为行政管理+民事合同两个部分,并结合案涉争议的焦点,判断案涉争议属于行政管理范畴还是民事合同范畴;而支持按行政性质审查的法院,一般不会具体到案涉争议焦点层面进行分析,而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认定其属于行政性质。 为便于直观了解,摘取部分参考案例如下: 支持民商事性质的案例 【(2019)最高法民终789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前述BOT协议履行及清算所引发的纠纷,虽然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兴义市政府,但合同相对人威鲁公司、川建公司在合同订立、履行、清算过程中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不受行政行为单方强制。案涉合同内容体现了缔约当事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对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特征。且合同并非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所涉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内容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不因此影响合同性质的认定。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2018)最高法民终1319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新陵公路项目协议书》为BOT合同。BOT合同的基本模式是,由投资单位与政府签订合同,其中投资合同一方投资建设、运营项目,由相关政府部门授予特许经营权,以特许经营项目方式收回项目投资并获得收益。虽然BOT合同一方当事人是政府机关,但所缔约合同内容体现的是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属于民商事合同,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 【(2015)民一终字第244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河南省辉某县市上八里至山西省省界关爷坪的新陵公路,而开发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开发和经营新陵公路,设立新陵公路收费站,具有营利性质,并非提供向社会公众无偿开放的公共服务。虽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某县市政府,但合同相对人新某公司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本案合同并未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其他内容,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不能决定案涉合同的性质。从本案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看,合同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应当定性为民商事合同,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某县市政府主张本案合同为行政合同及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没有法律依据。” 【(2014)民二终字第40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交通局行政主体身份对本案法律关系的影响。首先,交通局行政主体的身份不影响本案争议的独立性。案涉《BOT协议》《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交织着相关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重叠,在民事合同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关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但该协议与其履行过程中所涉及的行政审批、管理事项等行政行为,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这些行政行为虽影响双方合作,但不能因此否认双方民事合同关系的存在及独立性。……其次,交通局行政主体身份,不能当然决定本案争议为行政法律关系。争议法律关系的实际性质,不能仅凭一方主体的特定身份确定。本案需判断争议是否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相关,应结合争议的具体内容及所针对的行为性质认定。” 支持行政性质的案例 【(2019)最高法行申14276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款(十ー)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行政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本案中,某区政府通过与恒通某方公司签订《哈尔滨至红星乡工程建设项目BOT合同文件》,将哈红公路的专有权(包括工程修建和商业运营)授予恒通某方公司,系典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因履行、解除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某国际有限公司、湖北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诉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解除特许权协议及行政复议一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协议系荆州市政府为加快湖北省高速公路建设,改善公路网布局,以BOT的方式授予某国际公司洪湖至监利段项目投资经营权,属于以行政协议的方式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在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过程中,不仅行政机关应当恪守法定权限,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履行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作为行政协议的相对方的某国际公司亦应严格遵守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否则行政机关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协议的约定,行使解除协议的权利。” 【(2024)鄂01民特323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收购框架协议》第十条约定:“各方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请协议签订地的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但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2021)鄂行终字第323号终审判决,认为“BOT协议为典型的行政协议,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及协议的合约性”。而案渉《收购框架协议》是基于《BOT特许经营协议》所产生的,《收购框架协议》是经江夏区政府同意,授权某乙公司与某某环境公司经过充分协商自愿签订的行政协议,而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协议。” 通过上述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及其他部分法院的观点可以看出,司法机关目前对于BOT协议的性质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态度截然相反。从支持民事性质的裁判文书看,法院并非简单以特许经营协议合同一方当事人是政府机关、内容涉及行政审批即认定纠纷属于行政案件,而是会依据特许经营协议的具体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争议事项、诉讼/仲裁请求等综合判断协议性质及案件性质;支持行政性质的裁判文书通常直接陈述BOT协议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行政协议,不做其他分析。此外,亦检索到近年未在裁判文书中论证BOT协议性质但直接按照民事案件审理的案件,出于篇幅考虑,不在此一一列举。 另外,2024年5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编制)范本(2024年试行版)》,其中最新的特许经营协议范本中第79条第2项“争议解决方式”规定:“除本协议另有规定,若在尝试友好协商解决后【】日内该争议未能得到友好协商解决,则除依法依规提起行政复议外,本协议各方可依法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但对于因甲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金钱支付义务或履行该等金钱支付义务不符合约定引起的民商事性质争议,争议应当被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填入仲裁机构名称)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可以看出,该条款中对于特许经营协议中的民商事性质争议进行了明确区分,即通过合同范本的方式明确了特许经营协议中可能包括民商事性质的争议,并应通过民商事方式解决。从范本看,虽然范本并非必须强制使用,但从内容上看,有关部门对前述性质争议问题做了简单切割,即案涉争议涉及金钱支付义务或履行该等金钱支付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为民商事性质争议;其他争议的,应当提起行政复议及诉讼。当然,该范本的区分较为简单粗暴,不能涵盖所有争议,但可以通过此了解有关部门对特许经营协议的态度——认可BOT协议中行政与民商的交叉性,应做区分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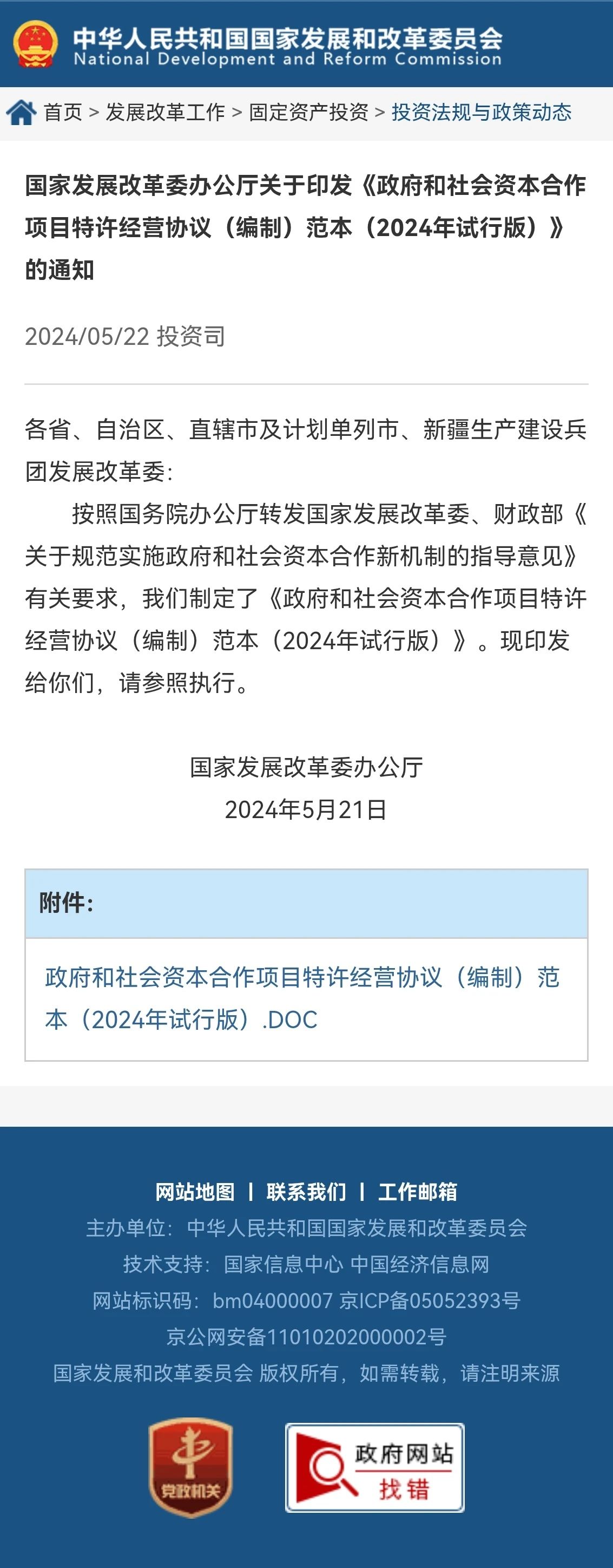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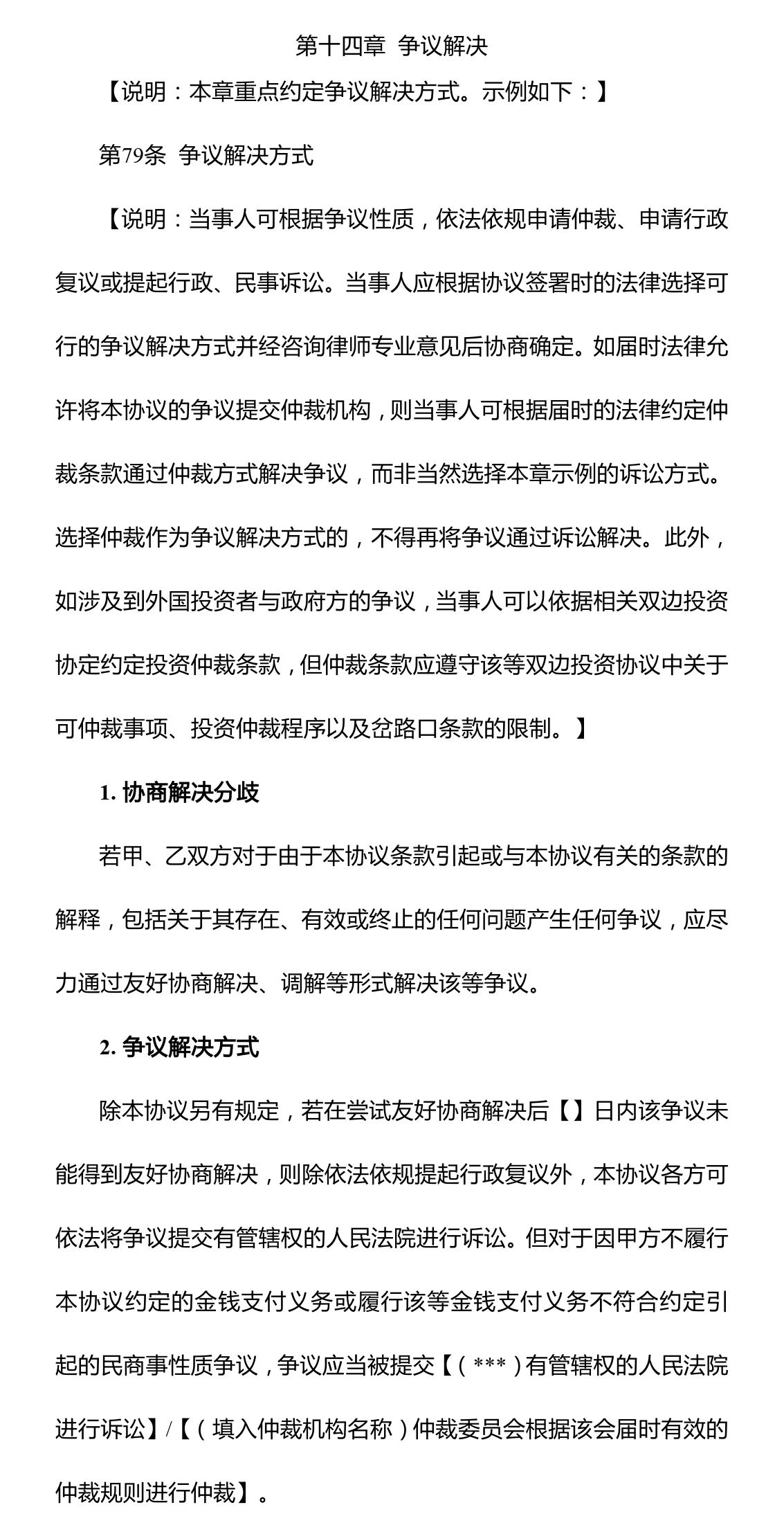
综上,从目前检索到司法判例的结果看,目前关于BOT协议的性质仍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从目前看到的司法判例,简单概括就是:按民事程序立案的,通常按民事案件处理,法院否定行政性质的抗辩;按行政程序立案的,即按行政案件处理,法院否定民事性质的抗辩,行政和民事审判庭对于同类协议性质的判断截然相反,这对后续案件的性质分析造成了一定困扰。笔者认为或许是立法较为笼统不足以涵盖每一个具体行为,亦或是立法者和司法机关本身对此尚有争议。为此,笔者曾与某高校行政法学专业人士浅浅探讨,其认为只要是BOT协议都应当属于行政协议,不需要看内容和争议性质;而与某法院立案庭人员沟通,认为要求政府方按约定支付费用应当按民事处理。具体哪种意见在法理上更合理,并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遇到具体问题时,需要通过分析论证从而选择最适宜自己的方式。笔者经过分析论证后认为,BOT协议无论是否名称是特许经营协议、是否包含特许经营的内容,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都不应简单地被认定为行政协议,如果其中体现了合同主体的平等性、权利基础来源于合同约定、项目具有营利性质,则应属于民商事合同,为“无名合同”。从亲身实践中看,目前BOT协议的纠纷仍可通过民事立案审理,且部分法院在立案时也会明确告知此类BOT纠纷属于民事案件。
(未完待续……)
©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 京ICP备18018264号-1